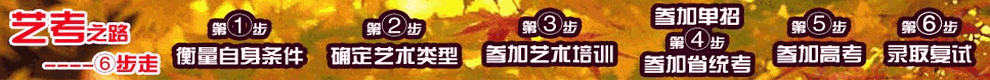|
对留学生来说,听西方人谴责中国是件痛苦的事,于是有些人成了活动家
11月15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2010门户开放》报告。报告指出,2009年至2010年度学年,中国首度成为美国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该协会会长艾伦·吉德曼说,中国学生数量之所以迅猛增加,是因为本科生人数大增。为了掌握流利英语,增强技能,进而在跨国公司或政府机构获得一份人人向往的职位,许多中国高中毕业生踏上赴美留学的征程。这些学生在美国面临的是怎样的校园生活?他们能否适应与中国迥异的美国文化?西方的价值观,以及美国校园的派对和吸毒文化会对他们产生何种影响?《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
“中国人打算投资一切能带给其优势的事物”
与父母的意愿相违,李婉容(音)暗中备考并赶赴离家3小时车程之外的香港参加了SAT考试(美国大学入学标准考试)。她对父母说,她要去香港购物。她的决心,以及德鲁大学提供的1.2万美元奖学金(它稍稍减轻了4万美元学费的负担),最终令其父母改变了主意。
李婉容是潮水般涌入美国大学的中国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虽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研究生院的现象早已有之,但赴美就读本科的学生近年越来越多。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09学年,有超过2.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读本科,较8年前的8000人大幅增加。
中国学生不只是在全美知名大学就读,还包括一些区域性高校,州一级高校,甚至还包括一些招收海外学生的社区学院。大多数学生支付了全额交通费用(海外学生没有资格获取政府资助),从而大大减轻了大学的负担——美国大学的捐赠资金及政府拨款因经济衰退而大幅缩水。
中国学生留美热潮,是与中国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同时出现的。在中国,越来越多跻身中产阶级的父母积蓄多年,供其独生子女上名校,以期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优势。 “中国人打算投资于一切能带给其优势的事物,拥有一个美国学位当然有助于提升在国内职场的竞争力。”国际教育协会副会长佩吉·布卢门撒尔说。
“美国人很好,但我没法跟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关系”
来自上海的罗格斯大学大三学生沈新超(音)之所以选择到美国上大学,是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和教授辩论,而中国大学并不鼓励这种行为”。在美国读书是选择专业,而不是考取专业。“在中国,当你走进大学校门第一天,你的发展路径几乎就确定下来了。”汉密尔顿学院大三学生丁英涵(音)也说:“中国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名好听众,而西方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名优秀的演说者。”
来自上海的袁携程(音)是佛蒙特大学的大二学生,其英语水平已相当不错。他加入了以语速和思维快速著称的辩论队。在每周的辩论会上,他就原住民土地权利和买选票等话题与对方辩友展开辩论。在不到7分钟内陈述一种观点,这对于他以简洁的文笔撰写学术论文大有裨益,而且使他开始以质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辩论的要义在于以一种我在中国从未想过的方式挑战现状,思考更好的解决之道。”
但美国的大学生活也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上大一时,沈新超发现校园生活孤独且疏远。他跟另一名舍友合住一个房间时,这名同学当着他的面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自由,非常残暴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沈新超说。他现在已经搬出校园,跟几名中国朋友合住在一起。“美国人很友好,但我就是没办法跟他们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或许最令中国学生不安的是美国校园内强大的活动家文化——美国年轻人常常在战争、民权和移民等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听闻西方人谴责中国或许是件特别痛楚的事情。于是,一些中国学生自身也变成了活动家,对西方人指责中国政策的声音给予反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愤怒的中国学生与试图破坏美国火炬接力活动的抗议者对峙。中国学生有时也十分罕见地对校园内亲西藏活动家进行骚扰,并设法阻止所在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来学校演讲。
“我不想在酒吧里醉醺醺地跟人消磨时间”
参加派对是美国大学生必经的入学仪式,而中国的社交活动通常围绕着桌子进行:三两密友一起做饭、吃饭或玩游戏。站在一个塞满陌生人,回荡着刺耳喇叭声的房子里的乐趣是中国学生无法体会的。
在汉密尔顿学院,丁英涵时常惊讶于周围耀眼的财富。他说,一些学生经常乘直升机赴曼哈顿度周末,开派对时喝的是香槟,而不是啤酒,抽售价100美元的香烟。对于一年只理几次发(因为对于父母来说,15美元的费用是一笔大钱)的他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齐帆(音译)最先在中密歇根大学就读。刚一安顿下来,他对美国的神秘感就逐渐消失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即使美国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室友是一名黑人和一名白人,分别用不同的口音与他交流,社交圈子也大体上与各自的肤色相配。有时,他们会把齐帆从床上拉起来,拖着他参加派对,玩一晚上啤酒桌球赛。
然而,齐帆不喜欢“特别看重饮酒”的校园文化。上大二时,他转入了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他对这所大学非常满意,时常驾驶刚买的轿车去纽约市游玩。但为了避免涉入饮酒文化,他跟其他中国学生合住在校外。
来自天津的弗朗西斯·刘是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她现在依然记得上大一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朋友们开始吸食大麻,随后给了她一个烟卷。“她们说,‘弗朗西斯,来呀’。”她拒绝了。但试图融入的压力意味着她不得不熬过许许多多的深夜。“我不想在酒吧里醉醺醺地跟我从未见过,也不愿再见的人消磨时间。” “我已经试过了。大一时每个单周周末我都去参加派对,但我觉得这种场合不适合自己。”
周可惠(音)现在是杨百翰大学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她是在父亲一个好友的推荐下,选择这所大学的。该校商学院的排名非常靠前。其父母认为,这所大学严厉的行为准则可以提供安全保障,让自己的女儿更加专注地学习。然而,刚来时,宵禁制度和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严禁学生穿短裙、饮茶)一时让她不知所措。
“起初,我的确很难接受这些条条框框。”周可惠说。 “在我的家乡福建省,喝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校园散步时,经常会碰到某个白衣修女走过来,开始用中文跟我攀谈。”慢慢地,这种温暖和共同体验让她相信,选择杨百翰大学是正确的。
东西碰撞:我被卡在中间地带?
不喜欢派对的弗朗西斯·刘在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找到了庇护所。耶鲁大学这栋用透光云石建成的立方体建筑收藏了数千件世界上最珍贵的手稿。去年夏天,她在那里当助理,主要工作是把需要的文本送交研究人员。除了12美元时薪,这份工作更让她满意的地方在于,她时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极为珍贵的手稿,比如伊迪丝·华顿所著的《纯真年代》,而且还能尽情浏览古朴华美的9世纪羊皮纸文献。“18岁时能用手指触摸历史,的确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一年后,她相信,自己再也不是当初穿过耶鲁大学哥特式走廊时那个沉默寡言的亚洲书呆子了。现在,她化妆,上课时举手,持有跟其中国朋友迥异的观点。在朋友看来,“我已经被美国文化腐蚀了,不再是中国人了”。
许多在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听到过类似的评语。在耶鲁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的文学研讨课上,徐露伊(音)开始应对“将我迅速西化,驱使我远离自身文化背景的拉力”。“不知咋的,我被卡在了中间地带,无法对任何一方产生认同感。”这名来自上海的学生是班上唯一一名国际学生。她并没有忽略自己的“异类身份”,而是深入这门课程,探索身份建构和身份混淆等问题,阅读移民和流亡者撰写的指定读物。
最终让她感觉如家般舒适的地方,是她的宿舍。居住在一栋楼的女生们每隔几周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饼干,谈论大学生活,解决女孩遭遇的“戏剧性事件”。弗朗西斯·刘说,这类“女性圆桌攀谈是一种非常棒的建立人际关系的体验,也是一个沉思自身经历的好机会”。(任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