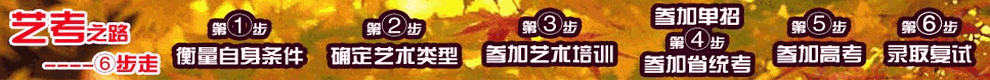|
二、耳识在访谈和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顾名思义,“访谈”与“交流”绝不是一方的主观能动,而是有问有答有来有往的双向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节目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访谈和交流的过程中,主持人不能单纯的只动嘴巴而不用耳朵。
听,首先是一种尊重的态度。新闻题材的广泛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访谈对象的丰富性,虽然这些人的思想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所有这些受访者都希望在一个平等的氛围下进行交流,没有人愿意处在被支配的地位,更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形象在媒体上被矮化或歪曲。“倾听”是主持人与人为善的外化,也是请对方打开言路的一种期待。主持人不仅要根据节目预定方针进行有目的提问,不仅要用眼睛观察对方的神态举止,还要通过耳识从对方的音色、音高、腔调、语速中去分析对方语言背后的东西,通过“察言观色”,引导话题的继续深入,从而与被访者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曾说,访谈的核心目的是得到新闻事实,主持人要给对方说话的权力,再对话题的流向进行宏观调控,适时引导,就是要起到化学反应过程中“催化剂”的作用,让对方发出火花,烧出光亮。
听,还是一种技巧。当遇到交流阻力时,真诚的倾听就变成了与访谈对象沟通的点化剂。主持人的倾听会逐渐为对方培养起美妙的成就感,他会认为你是一个愿意倾听他的故事、愿意接受他的思想的人。一旦双方能达到这种心灵互动,那么你距离想要得到的答案也就不远了。同时,“倾听”也会让你真正地投入到谈话当中去,了解更为全面的信息,说不定就会出现意外收获。
著名节目主持人、表演艺术家王刚在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受聘仪式上谈到,作为主持人“学会倾听”很重要,尤其是访谈节目,与人交流时首先要做一个好听者。他说:“我很欣赏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陈鲁豫,她大部分时间在倾听,偶然说一两句话往往说到点子上,这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倾听是需要耐心的。从现实角度讲,很多主持人不是一个好听者。认真倾听是对人的尊重,在对方说的差不多了,或你认为可以插嘴的地方再插嘴,不可忘记自己是做什么的。”
美国CNN著名主持人拉里·金曾说过,真正健谈的人不都表现在“谈”上,也表现在会“听”,听后能把握住要点,紧跟追问。他认为要做好访谈,首先要善于倾听,想要别人对你感兴趣你要先对人家感兴趣。只有仔细倾听,才能适当回应。拉里·金说:“我每天早晨都提醒自己一条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不管说什么话,自己什么都学不到;要想学到什么,只有多听。”
三、耳识在接受受众反馈过程中的作用
虽然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当属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个特殊的岗位并没有赋予播音员主持人个人以高高在上的特权。要想成为真正受受众欢迎的播音员主持人,则要有较强的平民意识,应时刻关注和听取来自普通受众的声音。
笔者曾闻听一些基层媒体播音员主持人的故事,他们在“自己的地盘”里大都算得上小有名气,有的甚至已经成为当地时尚的代言人,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广播电视充分利用开路、闭路、卫星、数字等高技术信号传输的今天,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大行其道的现实和受众眼前几十上百个频道并存的现状,不能不使我们节目和媒体的代言人——播音员主持人产生必要的紧迫感。因为受众不会因为你是基层媒体的播音员主持人而原谅你同样“基层”的水平。可以说,无论你是基层还是央视,遥控器面前,人人平等。
中央电视台在90年代初期就曾以电视主持人为切入点,提出“打造个性化主持人”的目标,由此在中国出现了如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等极富魅力和品牌效应的主持人。他们不断地强调和追求各种符号的个性化,就是像《焦点访谈》这样严肃性栏目,也要讲究诸如:人的表情要丰富,言语要注重人文气息,形态语言要有美学性质等,并将这些运作透明化。前几年视央还进行了一次“对主持人‘吹毛求疵’”的受众调查,受众对主持人的细节问题也作出了积极的反映。诸如说水均益动不动将脖子前伸,拉出一幅专家气势;说敬一丹动不动说她女儿怎么样;说白岩松什么什么等等(2)。
这些不但充分反映着受众地位的提高,更说明明智的媒体决策者和聪明的代表媒体形象的播音员主持人已经知道要降低姿态,躬身听取来自最广大受众的声音,而不是盲目的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品质,实现更大效益。
作为播音员主持人队伍中的一名普通从业者,和许多人一样,笔者以往读到的大多是关于如何训练嘴上功夫和关于播音员主持人综合素质方面的专业论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拥有优秀的“耳识”对于我们这个行业中人来讲,与有着优秀的外型、头脑和嗓音一样,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和意义。
在此希望,我们每一个同行都能通过努力,在广播电视这个特殊的领域,掌握“听音辩器”的绝技,“听”得更清、“说”得更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