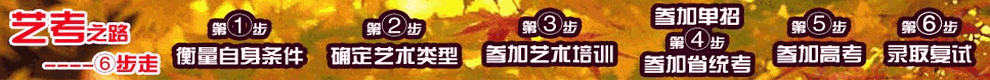|

李咏出生于新疆,祖籍在山东,正好是中国版图上的东西两端。在新疆出生,也在新疆长大,李咏与山东并没有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日后的升学,抑或工作,辗转于各种表格之中,在籍贯一栏上,李咏也总是填上新疆,而不是山东。长在红旗下,接受的是新中国的国家观念教育,从山东到新疆,或许并不算是一种漂泊。虽然如此,并不表示李咏就是很喜欢在新疆的生活,“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新疆,我都说不出为什么,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我老想逃跑。”这种不喜欢没有理由,也并非一种背井离乡的失根状态造成,想逃离一个地方,想“生活在别处”,似乎来自于一种诗人的气质,它是莫名的,正如忧郁可以毫无理由地突然降临。“尽管家庭生活挺温暖,可我的心态特别不对劲,尤其上了初中以后,老想离家出走。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因为家里对我疼爱备至,呵护有加,所以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于是,就不管不顾地变得特别自闭,整天独来独往,谁也不理。”
“我18岁去北京念书之前,连乌市都没出过。更别说什么去游览吐鲁番、敦煌、天池等名胜了。”
“我爸我妈1958年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就去支边了。我们家的生活还是比较稳当幸福的,父母是很传统的人,我还有俩姐姐,家里人都很疼爱我,我呢,内心的想法可能就比较各色。”也许正是一种“稳当幸福”的环境,使他觉得周遭的空气变得凝滞,生出了逃离的念头,在“传统”与“稳当”之间背叛出去,寻找一个新鲜的环境,一个出口。
这种沉默与孤独具备了艺术家的某些品质,因为在孤独与沉默之中,人的内心沉潜进最深处,达到一种想象的自由飞扬。
“上中学的时候我沉默寡言,跟谁都说不上话,心里说不出的烦,所以大多数业余时间都在画画,整本整本地画素描、速写、水彩、水粉,后来还画油画。我爸倒是早就看出我对画画感兴趣,(因为据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带我看京剧《十五贯》,回家我就画了一夜乌纱帽),就带我去跟一位很好的老师按专业的方式学画。”
在著名主持人的身份之外,李咏还担当着一个业余画家的身份。成为一名专业的画家,曾经就是他的梦想,在那个时候,他喜欢背着画板整天在街上乱走,捕捉灵感之余,也打发了孤独的无聊时光。乱走乱画,他的绘画功底也逐日精进,据说,以他当年的水平,考上西安美术学院应该没有问题。而后来,为何又放弃了这个梦想?原因在于有一天,他的启蒙老师告诉他,绘画讲究“血统”,如果没有这个画画的天分,还是把它当作业余爱好为好。这个忠告使他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为了未来的前途,他需要另谋他途。从这个往事也能见到,李咏对于自己的绘画天分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虽然自信能考上西安美术学院,但对于未来能否在绘画中有所成就,他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假如他没有听从启蒙老师的劝告而执意以绘画为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李咏这个家喻户晓的优秀主持人将要存疑;但是,同样,最后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李咏,是否也断送了成为一名著名画家的可能,同样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一个念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但不能确定它就会成为现实。最后放弃画家梦的李咏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他具备了成为一名主持人必要却又不充分的条件,矛盾,用在李咏身上再贴切不过,李咏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矛盾体。
即使后来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李咏也经常在周末的时间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这是一种爱好的抒发,也仿佛是一种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一种依依不舍。工作之后,失去了读书那种单纯的环境,工作忙碌,杂事也多,要重拾过去的绘画爱好,没有时间,也丢了心情。
艺术陶冶人的心境,绘画需要凝神,需要静心,需要捕捉灵感,在一丝一毫中萌发神来之笔,一笔一画都是功夫。虽然已经失去了成为一名画家的缘分,但如果有机会,他很喜欢重拾绘画带来的那种快乐。“一次我们《非常6+1》剧组去一个建筑设计院寻找一位选手,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在画人体画,我本来喜欢国画,所以和那位老师聊天聊得很投机,我们一聊就聊了一个多点呢!虽然我现在不能画了,但我觉得画画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它对我的审美、穿着、思考都有指导作用的。”
正因为会画画的缘故,李咏意外地当上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职位不低。当时他还只是高一的学生,自认为沉默寡言的李咏很难想到他担任的竟然是以宣传为己任的宣传部长。
这个“干部工作”,同样意外地使他与广播、主持产生了联系。
“当宣传部长的第二年,我又负责在学校广播站念稿。运动会上稿儿最多,一般都是这样的:‘初三二班来稿:同学们,看呐!运动员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了起跑线,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哇,加油,加油,加油!’”
宣传部长的工作虽然简单,却同样是一种历练,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启发,以及机会:“说来真是巧,我们学校有一个教音乐的老师,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的还是花腔女高音。你想她满腔的抱负,却在一个职工子弟中学教书,当然是不得志,于是整天支棱着耳朵寻找可造之材,以传承自己的艺术。在听到广播站喊‘加油’的时候,她觉得我嗓子不错,就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声带,然后就教我。她让我听帕瓦罗蒂、多明戈,给我讲《茶花女》,还每天下午让我站在洒满阳光的窗前,拿个带子勒住我的小腹,听我发声。她一边听,一边细细观察我喉结的运动,是升了还是坠了,那个情景简直像一幅画儿一样,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后来做扩展音域训练时,我爬音爬得很快,到高三时我已经唱到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课程了。老师非常兴奋,一心想把我培养成男高音,送进中央音乐学院,不过最后,我上了广播学院而不是音乐学院,我的老师,她流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