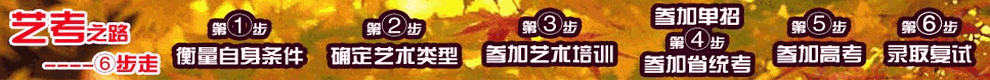|
浙江在线 10月12日讯 有些老先生的身影,如同一杆标尺,让我们得以清晰丈量。
75岁的章祖安,便是这样一位先生。
在中国美术学院这样一个高人辈出的校园里,他一直被视为风骨清异――因为他不偶不群,脱凡出众。
在他早年的求学经历里,师从陆维钊(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夏承焘(著名词学大师)、王焕镳(著名文史学家)、姜亮夫(国学大师)等大家。
而这些先生,又秉承梁启超、王国维、柳诒徵、吴梅等一代国学大师之风骨。章祖安的国学修养,可谓一脉相承。
任教后,他又伴随陆维钊先生,参加中国首届书法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学,后成为中国美院首任书法博士生导师。
当今浙江书法界的领军人物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章祖安就已经是老师了。所以,到现在,这些书法大腕们看到他,都要尊称一声“章先生”。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曾这样写他:奇人、奇遒、奇狷。
奇人,指的是他文武双全。中国传统学问与文章,他信手拈来;而其始于6岁的童子功,也使得他年逾古稀,却鹤发童颜,目光如炬。
奇遒,指的是他的书法艺术。他文武兼修,最后归于书艺。
奇狷,是他因秉承文人忧患情怀,又坚持真我性情,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会因率真犀利而叫人尴尬,但了解他的人却极爱他。其实,他是很可爱的,看到窗外梅花被雪压断,也会忍不住伤怀。
当记者见到他,才真正体会到“三奇”。
75岁的老先生,在深秋的天气,依然是短袖汗衫一件。用手机敲起短信来,利索不含糊,用“梢青女史”称呼记者,叫人不知所措。
他说,这是对有文化的女性的尊称,又叫人愧不敢当。
如今已很少能在美院看到章先生了,但传奇却在风闻耳传中不绝。这样一篇访谈,或许,能够让更多人洞见,一个真实的章先生。
章祖安先生一头银发,气宇非凡,最特别的是那一双眼睛,似能将一切看穿。
在这一双眼睛里,最深刻的是那些名师的印迹。在大师渐行渐远的今天,章先生总是对学生说,我们这辈人要比你们幸运得多。
在那样的耳濡目染、血脉相承中,今天,他也成为后辈们敬畏景仰的“先生”。
许江说:描述章先生艺、人风貌,由学养到书艺,再到风骨,并不是神话他,而是希望在当书法成为“万人之艺”,却容易流于图形笔划表象的时代,刻划一位老学者真正的一面,追访其学问与风骨的内涵,以期还原中国文化人平中见奇、卓尔不群的个性形象。
而这,也是这一个下午的访谈间,聆听老先生一席妙语之后的真切感受。
(以下记者简称“记”,章祖安简称“章”)
【家学】白天描红,晚上练功
章祖安6岁时,父亲为连续丧子所惧,命其随武师习武。不久,河北保定王姓武术家持介绍信来到家中,自此为专门教席,入住家中数年。
同年入家塾,识字并诵习《幼学琼林》等,开始描红习字。
记:听说您小时侯的家境很不错?
章:我父亲是清朝的官,而我是1937年出生的,所以他的官职跟我毫无关系。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当时刚好抗日战争爆发,家里也一点点败落。
记:家庭给了您正统良好的教育,您小时候接受的旧式教育是怎样的?
章:总的来说就是每天背古书。
念书前我父亲领着我坐黄包车到一个地方去磕头――先拜孔夫子,再拜老先生。拜好之后我都不知道这个老先生是谁,估计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人。
回家后,就意味求学开始了。
6岁我就开始描红了。我们小学里除了算数用铅笔,其余全都用毛笔。还要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天一张大字。
记:您一直练习武术到现在,为此受益不少吧?
章:练武是父亲为了让我强身健体,教我的王师傅都是在晚上教,叫夜功。
从立正开始教,站着一两个钟头不动。最痛苦的是扎马步,到最后汗流浃背。练几天以后,路都不会走了,然后再教拳啊什么的。
习武的习惯我一直有保持。
2006年在卡塔尔的多哈机场转机,所有人都穿很多,我还是一件短袖。
我基本上不感冒,而且坚持洗冷水澡,一直到2008年。
【师承】追随的老师声名显赫
1956年8月,刚刚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并任教半年的章祖安,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陆维钊、夏承焘、王焕镳(音biāo)、姜亮夫等老师。
毕业次年,经陆维钊先生提名调入浙江美院中国画系,任陆先生助教,教授全校古典文学、中国画系古典文学,开始正规的书法训练。
记:您1956年进入杭大中文系,当时的大学是怎么样的?
章:水平很高,都是大家,我是运气好。
陆维钊、夏承焘、姜亮夫教我们古典文学,有的教诗词,有的教古文,有的教语言。
当时学校氛围比较开明,有各种运动器械,每周还有交谊舞。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吃也吃得很好。
记:那时的师生关系怎么样?
章:当时除了课堂,学生还可以去老师家里请教的。王焕镳和陆维钊先生家里,我都去得比较勤。
学校还特意为老先生们造了两层楼的宿舍,一人6间房,还有浴缸。
陆先生生活朴素,个性温和,但又严厉,时间观念特别重,我因为迟到被他狠狠骂过一顿。后来能够做他助手,是因为他觉得我的作业做得比较好。
我们那时对老师很敬畏,先生不会对学生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学生自己会做。
现在,由老师来要求学生,实际上已经完了。
我旧学的底子,就是在那时经过先生们的洗礼,和现代学术接轨了。
记:陆先生还曾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教?
章:王国维的助教他只当了不久,因为他很孝顺,祖父病重他就回来了。
王国维在学人心中的地位很崇高,所以,没有一直呆在王国维身边,成为陆先生的终身遗憾。
每次谈到王国维的自杀,他都很难过,总是说,假如我在,我会管牢先生,先生可能就不会死。
【见解】元气学养手艺,缺一不可
任教之后,章祖安就参加中国首届书法篆刻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教学,并于1996年成为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首任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
他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文,又融汇诸艺,文武兼修,最后归于书艺。
记:陆维钊先生原本的主业不是书法,但为什么能在书法上有成就?
章:主要还是一个审美问题。审美主要靠天赋,审美能力强的人,能自己审定字好不好。
现在很多书法家最大的毛病是他自己不知道好不好,没有判断力。
像我们追求的浑厚,有些人写出来是浑浊,就是因为审美不够。
我曾经说过,60岁以上书法还能往前走的人比较少,一般是往后退的。很多人40岁之前书法还可以,40岁以后变得越来越俗气。
书法好坏的判断标准,就在审美,而且是内美。
有些一开始觉得有震撼力,但越看越差。有些却能从整幅字的好,看到一个字的好,再看到一笔一划的好,渐入佳境,这个就进入品味境界了。
记:现在很多人提出书法技巧不重要?
章:到一定层面后就不需要再讲技巧,这和现在很多人说的不讲技巧是两回事。
现在很多书法家是半路出家的,技巧关没有过,就说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技巧怎么不重要?写书法必须先解决技巧。
林风眠(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对学生讲,画画不能看技巧,那也是对已经掌握技巧的人而言的。
所以,书法是有标准的,一定不能离开汉字,至于其它道啊哲学啊这些层面的东西,都建立在汉字和技巧的基础之上。
在我看来,书法还是一种精英文化。如果标准越来越模糊,什么都是书法,那么书法也就不存在了。
在解决技巧之后,作为最高一等的书法家,还必须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掌握,包括融合西方文化。
我有过总结:元气、学养、手艺,三者于书法家缺一不可。
记:沙孟海先生说自己一生都在打基础,不轻易谈创新,陆维钊先生甚至预言将来的书法很可能坏在创新上,你怎么看?
章:这个已经被不幸言中了。
我们常常提倡创新,但创新有这样容易吗?多少年才出来乔布斯这样一个人。
创新的周期很长,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创新不了,但目前书法还是存在创新空间的。
他身体特棒,爱吃蹄髈
讲述人:白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1987年我进美院念书法硕士,章先生是我的老师。1996年,他又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大家都很尊重他,虽然他是一个要求很高、非常严厉的老师,有时候甚至严厉得让人害怕。
记得有一次,一个学生迟到了,章老师就让他站在门口,不让进教室。他的时间观念很强,约好时间,晚个几分钟就要批评我们。
他不多写文章,不要求著作等身,但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思想、有观点。
他也有可爱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起哄,他就会即兴表演功夫给我们看。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毕业聚会的时候,他劈叉,把两只脚横搁在两个凳子上,中间是空的。
他还曾经扎着马步,用双手把一个高个子法国留学生举起来。他还可以用三个手指头就把一个五分钱硬币扳成90度。他大冬天只穿单裤,从来不穿棉毛裤。我们都自叹不如。
他也喜欢美食,一口气可以吃掉一整个蹄髈,还会和我们交流怎么烧怎么炖。不过这有时候,他就会被师母抢白:“你也就偶尔烧一次而已。”
他带着浓重的文化孤独感
讲述人:王霖,中国美术学院讲师
章先生看上去幽默风趣,其实他是个很孤独的人。
他对社会、对人的期待很高,比较不屑于平庸的东西。但他看到的总是事与愿违。
因为失望,他就躲得比较远。所以他很少参加各种展览活动,自己也不太愿意做展览。
去年他的个展还是我们学生鼓动,甚至有点挟持他的意思。
他的交友面很窄,因为他觉得宁缺勿滥,拒绝了很多无谓的、世俗的、功利的交际。
有时候他心里郁闷了,也会打电话给我,或者发来短信,牢骚一下。
我们常会相约躲到湖头山脚,聊天喝茶一整日,而且往往就我们两个人,再多一个人,他就不去了。
我可能比一般人更了解他,他的内心是热爱并关切社会的,对文化、对国家有很深的情感,有着非常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
他带着浓重的文化孤独感,常常表现得玩世不恭。他几乎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甚至会以嘲讽犀利的姿态示人。
这时候,难免会引来争议。
其实他内心不是这样,古人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话用在章先生身上很适合。
只有真正的知交,才会了解他的内心,才会懂得他的矛盾、苦闷和忧患意识,也才会真正理解他那著名的“佛魔居”的含义。
章先生特别爱才。只要看到读书的好种子,他都很爱惜,特别愿意帮助他们。对于那些埋头学问、不通世故的学生,他总是既爱又怜,一则赞赏他们的淡泊勤学,一则也担忧他们会生计堪虞。
但最终,他还是会以“幽僻处可有人行”这样的话来加以勉励,毕竟真正的学术事业总是相对清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