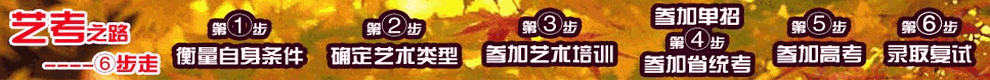|
一
刚到斯莫尔尼的时候,我简直是完全的手足无措。只能紧跟着眼前的一队国际学生,绕过蓝色的教堂和稀疏的树丛。十一月的彼得堡刚刚降下第一场雪,薄薄的一层铺在路面上,却又被寒风紧紧地卷着,打着旋儿飞走了。
暗灰色的天空,阴沉的教堂,风声呜咽着,启示着满眼的萧瑟与荒凉。
第一次去学校,我完全不知道该走哪里,该干什么。只是被彼得堡的华商张先生领着,慌慌张张地越过台阶,走廊,大厅里华丽的枝形吊灯……
办完手续之后紧接着就上课了。第一节课,坐在教室中央的是一个中年的黑头发的妇人,微胖。她自我介绍道:“我叫伊莲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俄国人,随后又陆陆续续地见到了胖胖的安拉,以及韩裔的俄国人娜塔莉娅。伊莲娜有时会非常凶,曾把我的一个女同学训的呜呜哭……现在这个同学已经从彼得堡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了。
安拉是一付心宽体胖的样子。有一次离放学还有一个多小时,突然学校停电了,安拉马上高兴地说:“那就下课吧,再见。”安拉教了我们一个月左右,就换去其他班了。然后我们这个班开始由娜塔莉娅接手。
我们班最初有五个人,除了我以外,其余都是高中毕业之后来俄国的。一个来自于深圳,一个来自于鹤壁,一个来自于开封,还有一个是新疆人,来自于乌鲁木齐。他们当中,深圳的和乌鲁木齐的学生最后一起去了财大(圣彼得堡财经大学),剩下两个一同去了交大(圣彼得堡交通大学)……
在斯莫尔尼开学第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班来了第一位女生,两年之后,她去了儿医(圣彼得堡儿科医学院)。然后来了第二位女生,是来俄国读研的,也就是她被伊莲娜训哭了。等到年底的时候,又来了三个学生,两男一女。他们最后一起入了师大(圣彼得堡赫尔岑师范大学)。
斯莫尔尼学校的宿舍楼位于瓦西里岛,船长大街3号,街的尽头是波罗的海。秋……冬……春……夏……
我们这些人住在那里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很多的人,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那里面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多得连数都数不清了。
二
斯莫尔尼学校的背后就靠着涅瓦河,离学校不远有座一百多年历史的桥。我常常在没有课的时候,步行去那座桥上转转。那时风和日丽,桥上车来车往。偶尔还能看见几只慵懒的海鸟,伫立在浮冰上,随波逐流。
学校一楼有个小型的图书馆,我在那边时,总是选择一个背对着所有物件的椅子坐下。图书馆里光线昏暗,每张桌子都固定着一个小型的台灯……尽管我用的那张桌子就挨着窗户,一旦太阳光照射进来时,我还是不得不把窗帘拉上。从那扇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庭院,里面生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
在斯莫尔尼能见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总是抱台笔记本电脑,围坐在走廊里上网的,是美国学生。大呼小叫,招群唤众,蜂拥出入,旁若无人的,是南韩学生。有来自欧洲的,当然,还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
我的教室坐落在二楼,临窗可以凭眺涅瓦河。旁边也有一个教室,那里面的学员年龄都比较大。詹姆斯,是个美国人,五十多岁的样子,想学了俄语之后,去做外交方面的事务。细谷徹,是个退休的日本工程师,六七十岁了,来学俄语纯粹是为了兴趣,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三桥秀彦,一个日本教授,曾在中国访问人民大学,汉语说得十分流利。他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国了。还有个日本记者,三十多岁吧,准备学完再调去莫斯科。一个意大利商人,会起身优雅地替女性开门。那些曾在我生命中或多或少留下印记的人,恐怕今生再也不能见到了吧?
……斯莫尔尼的新年晚会,那些光彩夺目的时刻,终生难忘。
三
列宾美院的预科生是斯莫尔尼一个特殊的群体,那是因为除了俄语课之外,他们还要面临专业课的选拔。在他们当中,一些人离去了,还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无论收获,他们的那段经历都是人生当中一段宝贵的财富……
涅瓦河悄无声息地见证了这些历程。
三月,四月,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那是在斯莫尔尼的日子里,唯一一次站在教堂的钟楼上,眺望彼得堡的四月天。天空漂浮着薄薄的一层雾气,使得阳光也显得格外的慵懒。远方,涅瓦河的水波静静地流淌。
伊莲娜走了,夏天来了,彼得堡的夏日,彻夜长明。娜塔莉娅还带着我们去过一个面包博物馆。那个小型的博物馆像是用一户人家改造成的,里面的展品毫不新奇,索然无趣。天知道娜塔莉娅那天为什么选定了这么一个地方。不过不久以后,她也休假了。
四
我在斯莫尔尼,从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到另一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总共九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期间,见到了很多人,结识了一些人,也在想念某些人。(摘自:俄罗斯《龙宝》;文/王骞) |